重新上传过去的文字,惊讶我年轻时期竟然这样写爱情。
2022年7月14日。
文/默许
许多梦,终于难了——题记
我叫靖。三岁那年母亲让我跟了继父的赵姓,从此我的名字就常常被人含含糊糊地喊成妖精。
当然后来真的成为人们眼里的妖精,大抵是和名字无关的。其实人自打一出生就注定了一切,该有什么该没有什么,该遇见什么人该走什么样的生死之门,都有命运的大手操纵,永远没有办法逃生的。
就象苏无法逃脱他的命运,就象我无法逃脱最初的孤独。
认识苏是在卫生系统举办的春节联欢舞会上,和慧挤在嘈杂的人群里,我不住地后悔。
“再埋怨,我骂你!”她转脸拉过一个人,“苏,这是我们产科最漂亮的妖精,今日让你有幸陪她。”
我尴尬。这三八居然一下子没入人群。
这时候音乐响起的正是《田纳西华尔兹》——我最喜爱的旋律。我将手交给他。他的手干燥温暖。
“不知道谁发明,必定如此姿态起舞。”我的眼睛越过他厚实宽阔的肩头。
“不然怎样?难道离你三尺么?又或者这样?”他突然以两手轻揽我腰间,“怕你更是不肯了。”
我轻带几分惊慌地望着他,脸上羞怯的表情正被他看在眼里。而两人之间由陌生而起的不适烟消云散。
其实也不是就单纯到没有故事的,可是一切故事随着毕业就已经结束,两个人一直到分离以后才明白,没有一种爱能够真正穿越时间和空间,海誓山盟不过是两个人发烧时说的梦话。可是,那种情感却成为一个标尺,爱情就定位在这样的高度,每次总不自觉地拿出来衡量。超越不了,宁可放弃。慧气急败坏地骂我是世界上最正宗的痴呆患者,我也懒得与她争辩。
“喂,专心一些,我可以保证至少给你一个愉快的夜晚。”
我转眼,苏的眼睛里除了微笑还有几分研究。这真的是一个不错的男人,体贴入微而不失唐突,举止温文却不失旷达;言语精练又不失幽默。可是,男人修行上乘,势必少不了身后有一位女子的千锤百炼。苏自然也不例外。
第二天早班,慧绕着我周围。
“哎,苏怎么样?外貌清秀洒脱,年轻有为,听说已经是他们附属医院心血管科的二把刀了。”
我在填写医嘱。
“昨天你走,他一直询问你的情况。”
“你现在按照医嘱去配好盐水。别忘了3号床病人手术后每隔一个小时要量一次血压。”
走到门口,我回头,“好男人都被女人抢走了,没抢走的也早就被预订了。这是我送你的忠告。别见了男人就眼睛发亮,三八。”
我闪身,一个棉球飞出来,擦身而过。
呵,我若肯终身对牢一个人厮守,白发苍苍的时候对着这一个人,一百次地埋怨一百零一次地唠叨;假如苏亦没有结婚,他倒不失为一个最佳伴侣,仅仅是舞在他的怀里,听着他低沉的絮语,已经够女人陶醉。可是,我对婚姻恐惧;而且苏也早非自由之身。
可是他的舞跳得是真好,快舞或慢舞,他的温和里夹带着一股霸气,令我身不由己地迷醉——或为舞,或为音乐。或者,为苏。
慧死缠烂打地拉我出去。泡吧,跳舞。每次都会有苏。我猜想她其实是为了他,慧毫不掩饰对他的好感。
现在这世界是这样的,太多人已经不再把承诺和责任放在第一,曾经拥有过,已经能够开心满足,幸福是什么?慧说幸福就是满足。那么满足一时就幸福一时,不断地满足是不是就会不断地幸福呢?所谓的幸福一生是不是简单到不断满足一生中的愿望呢?然而关于满足与幸福的问题始终没有人能够给我答案。
而每次聚会地点苏都选得十分精致,正和我心意,于是我安心尽责地做陪衬,每每心不在焉地听歌漫舞赏景,任心绪神游驰骋。可是苏的妙语连珠依旧零星地听进耳朵里,苏的儒雅落拓也令同行的伙伴黯然失色。不是不动心的,但我有我自己的原则。
然,每次看见慧倾慕地望着苏的眼神,我便将幸福与满足的问题拿出来问一遍自己。呵我不是慧,又何劳我杞人忧天?
可是人生有时候简直就是一个万花筒,不知道谁轻微一碰,便转出另外一个风景。譬如苏,譬如我。
那是在慧的生日party上,大家嬉闹一团。慧的脸上被大家涂抹了大块雪白的蛋糕,人鬼不分地傻笑。我以为她醉了,可是在洗手间里她透过镜子看着我,异常冷静。
“妖精,你这慵懒散慢的模样,难怪苏,连我也入迷。”她看我目瞪口呆,“没有你,他根本不加入我们的。”
那么他都是为我选择的聚会地点么,都是为我而歌为我而舞么,那么幸福与满足的问题不是慧的而真是我自己面临的问题么。我转脸望向苏,他的眼睛越过众多人正看着我。那么他的眼睛一直都追随着我么。我的心莫名其妙地疼痛。
轮到苏和我的,又是《田纳西华尔兹》舞曲。
“我故意的。这永远是我们的第一支舞。”在他的怀抱里,我轻盈地飞扬着,“除了慧,我也为你准备了礼物。”
“不。”
“我克制过,和自己斗争过,可是……”
“可是,时间地点统共都不对。”我接下去,“我们错过去了。”
可是我的心,抽搐地疼痛。
舞在他的怀里犹如一片叶子飘扬在风里,永远令我沉醉。我轻轻地闭上眼睛,梦想能够永远一直这样跳下去,永不停止。
可这是我和苏最后的《田纳西华尔兹》之舞——这最初和最后的一舞,常常令我有一种幻觉,仿佛和他有过无数次起舞,又仿佛一生,仅有一次。
其后,聚会的圈子里消失了苏的身影,而我依旧和慧他们四处浪费着过剩的精力与时间,如我们这样的大龄女性,因为寂寞,最不怕挥霍的就是时间,最怕挥霍着,也同样是一点点迫老的时间。
慧自然是少不了对我一番责骂,唾沫横飞,张牙舞爪。可是我尚有良知,做不来苟且之事;又极端自恋,怎肯委屈了自己?而苏,此情可待,他却当真义无返顾一去不回,竟更是令我心生崇敬与思恋。推杯换盏间,盛宴散场后,抑或是寂寞无言时,苏的身影时时浮现眼前挥之不去。
世上有冤家路窄之说,便有狭路相逢之事。半年后,我和苏意外地相遇在我们医院的电梯里。
那日自三楼去十一楼医务室,我一步踏进电梯,迎面款款而立着的正是日夜难以忘怀的苏,四目相对,错愕震惊之下,万语千言无从说起。一时间,电梯里的空气太静,仿佛能够听得见我急促的心跳声音。
“你好吗?”
我尽量放松,又转身背向他,“好,你呢?”
“是过来专家会诊。”他沉默许久,“来的路上就想,也许会遇见你……”
可是遇见又能怎样?平添如许烦忧,如许困扰。
电梯于沉默间飞速上升,即将到达八楼心血管科的时候,苏忽然出乎意料地伸出手扶摸我的头发,极慢极轻。刹那间,只觉有一股暖流由发根灌入肺腑,牵引出没顶的疼痛和苦涩。
“保重了。”
等苏擦身越过步出电梯间,我方才颓然倚靠在墙壁上深吸一口真气,恍惚过后,忽然忆起苏形容消瘦枯槁,相对良久,他却未曾回答我那一句问候。一抹脸,竟已是有泪。
以为我与苏,经过如此这般,从此必是山高水远,萧郎路人。可三个月后,慧突然对我提到苏的名字。
“去看苏吧,已经是肝癌三期了。”
怎么可能,怎么可能!我发疯一般再三再四地质疑,慧的眼睛里依旧是悲哀而坚决的肯定。
“去看看他吧,他太不在意自己,拖到现今才肯检查,却已经晚了。”慧拉着我一路奔他们医院。“他一直说不想见你,可你这个妖精不至于真那么狠心吧!”
然,这妖精行至苏病房门口,却嘎然止步掩面失声痛苦起来。不能不信了,一墙之隔的就是日思夜想的人,慧决计不会以如此下作方式来试我真心。由不得不信了!
所以生活永远是残酷无情且无从修饰的。那日见苏,并未有小说或影视剧里强颜欢笑的剧情,我只坐在他的床头不住地哭泣,而苏黑瘦的脸上虽是脱了形地消瘦,眉宇间并无半点恐惧与忧伤,却有一种无法言及的释怀与坦然。他镇静而缓慢地叙述着病情的发展。身为医生的我们心里都明了癌已恶化到腹水,接下去面对的是什么。
“疼痛的时候真的难以忍受。”他轻描淡写,“我们以前对病人总是回答,除了忍着没别的法子,轮到我自己承受,原来有些疼痛根本无法以意志忍受。”
他的微笑令我心折,而他的描述则更令我心痛。我只在心里将曾经令我骄傲的坚持反反复复地后悔,直悔到死。
假如可以重新来过,假如一切能够挽回,这样的话不止一次在心里反复出现又不断否决……已经失去的东西,已经不可能复得了。
为不再有遗憾,又或者完全是因了这行将诀别的情感,对于那个固守在不远处的、彼此都极其明白的终结与伤痛,我彻底放弃自己所谓的原则,终日陪伴苏的左右,将彼此从孩童起始的故事一直说到现今。
最经常的是这样的对白:
“不要再来了。听话。”
“呵我是妖精。”
“你何必这样自毁清白。”
可他妻子并不经常陪伴他。
“她要照顾孩子,我住自己的医院里很方便的。”语气里不是没有无奈的,顿了顿,“你以后也少来吧。”
这样的话他已经说过,但那日听着突然十分刺耳,我猛然伸出手握住他的,“我在那日慧的生日晚会上后悔过,在电梯里后悔过,如今,我不要再后悔。”
偏偏就那样激动地忘记了时间,只待响起了冷冷的声音:
“果然是一个妖精。”话一听在耳朵里,便知道这是苏的妻子了,我挺直腰与她对视,眼睛里并无半点愧疚与惊慌。
她衣着端庄,五官清秀,惟眉宇间透着冷漠与严肃,“眉眼里当真有一些风情,不过是因为难过遮掩了,未曾使出来吧。”
果然不愧为人师表,心里必是恨入骨髓,话语中却未有半点污秽。
我依旧无言而立。学到这般年纪,早已明白许多事情并非都可以仰仗他人理解。我既是决定站出来,这一关当是必不可少的教训。
可是苏却急切地辩白:“我要怎样解释你才肯信?”
看他红头涨脸,我竟宛然一笑。他看在眼里,又急:“你为什么不听我?这又是何必?”
她倒不再多说,冷脸地忙碌起来,可见虽是少来探望,对苏依旧是有情有义吧。家有幼童,先生绝症,一个女人遭受如此磨难,于今时今日不能不说是一种莫大悲哀。
告辞出来,觉得自己真的大约前生是一只妖精,与苏有着一段缠绵恩爱孽缘,今日千回百转转世轮回,只为与苏了却一桩心愿。
接下来,我依然如故天天去陪伴苏,安心做彻头彻尾的妖精,苏医院的同事及家人亲友络绎不绝的时候,我一副无所顾及满不在乎的坦然。苏的妻子开始和我有了简短的对白。
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,苏的病痛越来越严重,每次疼痛都是非人般的折磨。我开始用各种方法为他购买止痛药品,而我们都清楚,最后止痛药也终将失去效应。
那天赶去他那里的时候已经很晚。
苏独自一人坐于渐次浓重的暮色里,眼睛呆滞地望着窗外,仿佛灵魂已游离于他的肉体,飘荡于遥远不可知的地方。
我轻轻推开门,房间里若有似无地回旋着随声听里的舞曲《田纳西华尔兹》。
我握住他手,一直到乐曲结束。
暮色四合,我们默默静坐良久无语。
“你信不信来世?”
“我信。”我知道他要说什么。如果以前我不曾信过有来世今生,那么现在我宁可信有神灵会垂怜我们。
又隔了许久,我轻声说:“听慧说药乡亳州有一种药材比较有效,明日我坐早车去,当日就可返回。”
“不要太赶。”他又说,“给我削个苹果吃好吗?”
苹果太大,他的胃口已是吃不下许多。我与他分而食之。
“我不许你这样——”
我望向他。
“知道我的病,她始终与我隔离的。你这样——我怎能许你这样。”
一时间空气里有种令人窒息的郁闷。此情如许,我如何在意生死?我赌气又吃,赌气再吃。
他轻笑了一边看着,忽然伸出手极轻极慢地扶摸我的头发,良久,说:“不要太赶,我会等你。”
第二日去亳州依然非常赶,仿佛一直有声音不断地催促,其实内心里也明白这一份药材未必有用,可是若能够多些时日看见他,于我于他亲人必也是种安慰吧。
车去车回,到医院已是傍晚。
不要太赶,我会等你。然,苏所说的并非是在此等候我——他以昨日的那把水果刀刺入疼痛万分的腹部。来人发现时,已是血水浸透了床单。
从此,不停地出现在我的梦里的都是《田纳西华尔兹》。在苏的怀抱里,我轻盈得好象一只羽毛,悠悠地飞扬着。常常不愿意醒过来,闭着眼睛在黑暗里继续旋转着依恋着,而心却无比清醒地疼痛起来。爱一个人有多难?忘记一个人又有多难?这世界上是不是真的有孟婆汤,一口喝下去,忘记所有的前尘往事呢?
火葬的时候连苏的妻子也劝我不必出席。世人眼里我自是一个妖孽,不知廉耻不择手段地来取苏的性命。如此一个妖精,怎能不令众人侧目。
然,我和苏既是有约,我又如何不送他最后一程。
追悼仪式上一路居然无泪,也不管若干人窃窃私语。事毕,我悄然隐退,于远处仰天眺望那烟囱里腾腾升起的浓雾,心中一阵恍惚:说到底,苏究竟是真的曾经属于过我,还是仅仅只出现在我的梦里呢。
版权声明
原创作品,未经许可,请勿转载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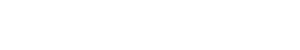
发表评论